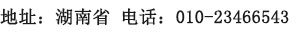文
吴学昭·主播
代号雾中花
杨绛走了,她带着破碎的山河和遥远的思念;
杨绛走了,她带着苦难的岁月和离别的哀怨;
杨绛走了,她带着无言的愁绪和寂寥的留恋。
杨绛没走,她留下淡然的笔调和荒诞的真实;
杨绛没走,她留下最贤的处世和最才的文字;
杨绛没走,她留下深沉的平静和悠远的笑意。
我们再见了,您们仨团聚了。
今天是杨绛先生逝世一周年,为了纪念杨绛先生,谨以此文,聊寄敬意。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年5月24日下午,医院看望杨绛先生,没想到这竟是我与老人的最后一面。
因为有些日子未去探视,保姆小吴见我走近病床,贴着杨先生的耳朵说:“吴阿姨来了!”久久闭目养神的杨先生,此刻竟睁大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嘴角微微上翘,似有笑意,居然还点了点头。
随后轻轻地嘟囔了一句,隔着氧气面罩,听不很清,意思应该是:“我都嘱咐过了……”
我从未见过杨先生如此虚弱,心里酸楚,强忍住几将夺眶而出的泪水,答说:“您放心,好好休息。”
杨先生已没有气力再说点什么,以眼神表示会意,随即又闭上了双眼。据一直守候在杨先生身旁悉心照顾的保姆和护工说,此后到“走”,杨先生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
不久,杨先生的侄媳和外甥女也来探望。内科主任及主管大夫请我们到会议室,介绍杨先生病情,说她目前大致稳定,但已极度虚弱,随时有意外发生的可能。
我还是一句老话,即使发生意外,请勿进行抢救。这是杨绛先生反复交代过的,她愿最后走得快速平静,不折腾,也不浪费医疗资源。
杨先生的身子暖暖的,手足却凉。小吴和护工不断摩挲杨先生的手臂使它热乎,又用热水为杨先生泡脚生暖。她静静躺着,乖乖地听任她们摆布不作声。
我盯着监测仪,不祥之感突如其来。时间已到晚上八点多钟,大大超过了探视时间,可我还想在杨先生身边多呆一会儿,后来经不住传达室同志的一再催促,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们为等候我们交还探视证、取回身份证,已耽误下班好几个小时了。
当日午夜时分,医院来电话报告杨先生病危。我和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项目部部长池净,还有杨绛先生遗嘱的另一执行人周晓红以及杨先生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所长,从京城的四面八方急急奔往协和,一心想着亲送杨先生最后一程。
但待我们到达病房,杨先生已经停止了呼吸。那是年5月25日凌晨1∶30,所幸老人临走没有受罪,有如睡梦中渐渐离去。
经过洗面、净身、换衣的杨先生,面容安详,神情祥和,就跟睡着了一样。
医院的值班副院长、值班医师、护士长、护士同志,与我们一起向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深深鞠躬道别。我们谢过了连日来为治疗护理杨先生辛勤劳累的医护人员,缓步推送杨先生去太平间安放。
杨绛先生遗嘱交代:她走后,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讣告在遗体火化后公布。
对于杨绛先生这样一位深为读者喜爱的作家、一位大众关心的名人,如此执行遗嘱,难度很大,首先媒体一关就不好过。
幸亏周晓红同志和我,作为杨绛先生的遗嘱执行人,在杨先生病势危重之际,已将杨先生丧事从简的嘱咐报告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恳请领导知照有关单位打破惯例,遵照杨先生的意愿丧事从简办理。后来丧事办理顺利通畅,全如杨先生所愿,实与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有关。
年5月27日清晨,医院的告别室绿植环绕,肃穆简朴。没有花圈花篮,也没张挂横幅挽联,人们的哀悼惜别之情,全深藏心底。
杨绛先生静卧在花木丛中,等待起灵。她身穿家常衣服,外面套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出访西欧时穿的深色羊绒大衣,颈围一方黑白相间的小花格丝巾,素雅大方。这都是按杨先生生前嘱咐穿戴的,她不让添置任何衣物。
化了淡妆的杨先生,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细眉高扬,神采不减生前,只是她睡得太熟,再也醒不过来。
尽管没有通知,许多同志还是赶来送别杨先生。这里没有前呼后拥,也无嘈杂喧哗,人人都轻手轻脚,生怕把睡梦中的杨绛先生闹醒。
起灵前,众至亲友好行礼如仪,将白色的玫瑰花瓣撒在杨先生覆盖的白被单上。我和周晓红等乘坐灵车陪伴杨先生去八宝山,陈众议所长留下向媒体发布讣告。讣告内容如下:
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一百零五岁的高龄于年5月25日凌晨1∶30与世长辞。
遵照杨绛先生遗嘱,她去世后,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在杨先生生前,她已将自己和丈夫的全部作品的著作权收益捐赠给母校北京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用以鼓励清华大学家庭经济困难但好学上进的学子,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并希望领受奖学金的学子学成后,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馈社会。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履行协议,在享有钱杨作品因使用而获得的财产收益的同时,有义务负责全面维护钱杨二人作品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相关权利不受侵犯。
关于许可他人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使用钱锺书、杨绛作品的权利以及钱杨作品的发表权,杨绛先生已委托专人行使。家中所藏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等,亦均作了安排交代,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执行人。
杨绛先生遗体已于5月27日火化。
从讣告看,杨绛先生生前对身后所有重要事项,已一一安排妥帖;与众不同的是,这一讣告居然经杨先生本人看过,并交代遗嘱执行人,讣告要待她遗体火化后方公布。
杨先生那种“向死而生”的坦然,对身后事安排考虑的睿智、周到、理性,往往使我感到吃惊和钦佩。
对于年老衰迈、死亡病痛这类话题,一般人特别是老年人,不喜欢也不愿多提,杨先生却不忌讳,不但谈论,且思考琢磨,体会多多。
我就听杨先生说过“病”与“老”不同:
她以为“病是外加的,临时性的,不论久病、多病,可以治愈。
‘老’却是自身的,是生命日渐萎弱,以至熄灭,是慢吞吞地死。
死是老的perfecttense,老是死的presentparticiple;dying也。
老人就是dying的人,慢吞吞,一面死,一面还能品味死的感受”。
杨先生自嘲当了十多年“未亡人”和“钱锺书办公室”光杆司令,已又老又病又累。可是她无论读书、作文、处事怎样忙个不停,永远都那么有条有理,从容不迫。
同住南沙沟小区的老人一批批走了,杨先生也等着动身;只是她一面干活儿一面等,不让时光白白流过。
为保持脚力,每天“下楼走走”的步数,从年的七千步渐减为五千步、三千步,由健步而变成慢慢儿一步步走;哪怕不再下楼,退到屋里也“鱼游千里”,坚持下去不偷懒。
日复一日的“八段锦”早课,年春因病住院才停做。“十趾抓地”还能站稳,“两手托天”仍有顶天立地之感,“摇头摆尾”勉强蹲下,“两手攀足”做不到就弯弯腰,“两手按地”则只能离地两三寸了。
毛笔练字,尽量像老师指导的那样,“指实、掌虚、腕灵、肘松、力透纸笔”,少有间断。只是习字时间,已由原来的每天九十分钟步步缩减为六十、三十、二十分钟,直到后来无力悬腕握笔。
杨先生这“钱办”司令真是当得十分辛苦,成绩也斐然可观。
《钱锺书集》出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订》出了,《钱锺书英文文集》出了,《围城》汉英对照本出了,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包括《容安馆札记》(三巨册)、《中文笔记》(二十巨册)、《外文笔记》(四十八巨册,附一册)在内的皇皇七十二巨册的《钱锺书手稿集》,竟于杨先生生前全部出齐。
很难想象,杨先生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以上每部作品,不论中英文,杨先生都亲自作序,寄予深情。
还有,钱锺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珍藏多年的谭复堂(谭献)《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也出版了。杨先生因为手札珍贵,担心丢失,不想拿出家门,宁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登门扫描。连续十多天,她让出起居室供人文社同志们工作,自己躲进卧室读写。
杨先生在忙活钱著出版的同时,不忘自己一向爱好的翻译和写作。她怀着丧夫失女的无比悲痛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她仔细研究原著多种版本的注释,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而力求通达流畅。她成功了,把这篇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斐多》出版后,杨先生私下说,她原来倒没想深究灵魂死不死,而更想弄清“绝对的公正”“绝对的价值”究竟有没有?如今不是仍在讲“真、善、美”吗,是非好恶之别,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
杨先生思念女儿,又写了《我们仨》,在点点滴滴的往事回忆中,与锺书和圆圆又聚了聚,写到动情处,泪滴溅落纸上。
《走到人生边上》,则写得不那么顺当,有过周折,颇费心思。听杨先生说,此作起意于她九十四岁那年,立春之前,小病住院。躺在病床上,闲来无事,左思右想,要对几个朋友“人死烛灭”“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的一致信念来个质疑。
没想到一质疑,便引发了许许多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从未想过,有些还是经常想的,只是不求甚解,糊里糊涂留在心上。
糊涂思想清理一番,已不容易,要一个个问题想通,就更难了。不料问题越想越多,好似黑夜走入布满乱石的深山僻径,磕绊跌撞,没处求教。
自忖这回只好半途而废了,但是念头愈转愈有意味,只是像转螺丝钉,转得愈深愈吃力;放下不甘心,不放又年老精力不足。正像《堂吉诃德》里丢了官的桑丘,跌入泥坑,看见前面的光亮却走不过去,听到主人的呼喊又爬不起来。
杨先生说:“我挣扎,这么想想,那么想想,思索了整整两年六个月,才把自以为想通的问题,像小姑娘穿珠子般穿成一串。我又添上十四篇长短不一的注释,写成了这本不在行的自说自话。”
她为台湾出版此书的繁体字本写道:“我这薄薄一本小书,是一连串的自问自答。不讲理论,不谈学问,只是和亲近的人说说心上话、家常话。我说的有理没理,是错是对,还请亲爱的读者批评指教。”
此前及其后,杨先生的《文集》《全集》先后面世。出版社营销部门的同志出于职业习惯,总想弄个研讨会什么的热闹热闹,或请杨先生上上电视、做客网站,吹吹自己。他们好心,却不清楚,这对不喜张扬的杨先生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年9月,杨先生将家中所藏珍贵文物、字画,还有钱锺书先生密密麻麻批注的那本韦氏大字典,全部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移交时,周晓红和我在场,杨先生指着起居室挂着的条幅字画,笑说:“这几幅虽然已登记在捐赠清单上,先留这儿挂挂,等我去世以后再拿走,怎样?免得四壁空荡荡的,不习惯也不好看。”
国博同志立答:“当然,当然。全听您的。”
遗嘱已经公证。书籍、手稿等重要物品的归属,也都做了交代。所收受的贵重生日礼物,杨先生要我们在她身后归还送礼的人。其他许多物件,一一贴上她亲笔所书送还谁谁的小条。
为保护自己及他人隐私,她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毁了许多友人的来信,仅只留下“实在舍不得下手”的极小部分。
杨先生后来也像父亲老圃先生早年给孩子们“放焰口”那样,分送各种旧物给至亲友好留念。有文房四宝、书籍、墨宝,也有小古玩器物等等。
我得到的是一本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年版的THEGOLDENTREASURYOFSONGSANDLYRICS(《英诗荟萃》),杨先生在此书的最后一页写道:“学昭妹存览绛姐赠。”
我惊诧于杨先生的神奇:我从未跟她提及喜读中英旧诗,她竟对我与她有此同好,了然于心。
我深知这本小书有多珍贵,它曾为全家的“最爱”,原已传给钱瑗,钱瑗去世后,杨先生一直把它放在枕边,夜不成寐时就打开来翻阅,思绪萦怀,伴她入梦。许多页面,留有她勾勾画画的痕迹。
我得到的另一件珍贵赠物,是一沓杨先生抄录于风狂雨骤的丙午丁未年的唐诗宋词,都是些她最喜欢的诗词。第一页上赫然写着:“文革时抄此,入厕所偷读。”
我能想象这一页页用钢笔手抄的诗词,当年曾被她贴身带入劳改厕所,在清理打扫之余,“猴子坐钉”式地蹲坐便池挡板上,偷偷诵读,自娱自乐。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我怎敢领受?可是杨先生执意说:“拿着,留个纪念!”
杨绛先生表面看似理性、清冷,其实她是很多情的。她一向把读者当成朋友,把理解她作品的读者视为知己。
她存有许多讨论她作品的剪报。她拆阅每一封读者来信,重视他们的批评建议。她对中学语文教师对她作品的分析,发出会心的微笑。孩子们听说她跌跤,寄来膏药,让她贴贴。
许多自称“铁粉”的孩子,是由教科书里的《老王》开始阅读杨绛作品的。有位小青年因为喜爱杨先生的作品,每年2月14日,都给她送来一大捧花;后来他出国留学去了,还托付他的同学好友代他继续送花,被杨先生称为她的“小情人”。
前些年,她还常与读者通信。她鼓励失恋的小伙儿振作,告诉他:爱,可以重来。她劝说一个绝望的癌症患者切勿轻生,而要坚强面对,告诉他忧患孕育智慧,病痛也可磨炼人品。她给人汇款寄物,周济陷于困境的读者而不署名……
杨先生走后,我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一大袋已经拆封的读者来信,多数来自大陆,也有“台粉”“港粉”还有“洋粉”寄来的。杨先生在许多信封面上,批有“待复”“当复”……最后可能都没有作复。
这里,我想借此文之一角,向杨先生亲爱的读者朋友说声“对不起”。杨先生最终没能如你们所愿,和大家见个面、回封信,实在是因为她已太年老体弱,又忙,力不从心了。
她感谢你们的关心、爱慕和呵护,给她孤寂的晚年带来温暖和快乐。在她内心深处,真的很爱你们!
年7月,杨先生百岁生日前夕,同意在《文汇报·笔会》上作“坐在人生边上”的答问,也正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说说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人生感悟,向亲爱的读者最后道别。
今年春节,医院度过的。旧历大年初一,我去协和探视,床前坐坐,聊聊家常。末了杨先生又交代几件后事。我心悲痛,不免戚戚;杨先生却幽幽地说,她走人,那是回家。要我“别太难过,说不定以后我们还能在天上再聚聚呐”。
年5月27日上午9时许,我去八宝山送杨先生回家。当电化炉门“咔嚓”一声关闭,杨绛先生浴火重生之际,我脑海中突然冒出杨先生上述那话。
我知道,杨先生不信上帝,也不信佛,她之所以有时祈求上苍,不过是万般无奈中寻求慰藉,也安慰他人。
她仿佛相信,冥冥之中,人在做,天在看。
然而不论如何,我宁愿相信灵魂不死,但愿有朝一日,还能与这位可爱的老人在天上再聚聚。
年7月30日午夜
作者简介
吴学昭,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听杨绛谈往事》作者。曾任《中国儿童》主编,《中国少年报》副秘书长,新华社、人民日报驻外记者,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本文首发文汇笔会(ID:ibihui)。有书经授权发布本文,转载请联系作者。
主播简介
代号雾中花,喜马拉雅电台签约主播。长春电台主播,专业配音人,节目策划人,播音主持专业讲师。微博:
代号雾中花,帮助白癜风公益医院白癜风医疗的饮食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