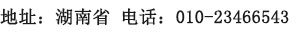三个小时的飞机,三个半小时的汽车,在去往粤西边陲的封开小城的路上,我翻来覆去地背诵着Anaesthesiologist之类的生僻医学单词,感觉回到了二十年前考托福GRE的日子。事实上这趟旅程是参加给兔唇或唇腭裂的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手术治疗的医疗活动,毕马威已赞助手术十多年,历年有多名KPMGer作为志愿者参与其中。这次我领到的任务是在复苏室为国际志愿者翻译,我心里琢磨,除了要命的单词外,这应当是一趟轻松的差事吧。
到达封开,撸起袖子,开工。同行的60多名志愿者,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医护工作者,手术医师、麻醉医师、儿科医师、手术室/复苏室/病房护士,个个都是让我敬仰的专业人士。作为一个工龄十八年的老审计员儿,混迹于这群医疗专家中,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和大脑的代码每天都在被不断刷新。一周之后,经同屋护士美眉速效培训,我成功晋级护士界新秀。新技能get的同时,随我一起回到北京的,还有满脑子的惊叹和感悟。
原以为审计是
最辛苦的行当
第一天做病人筛查,要从各地闻讯赶来的多例病患中筛选出满足手术条件的病人。我和我的翻译对象,来自美国的亲切护士Jean,战斗在长长的筛查流水线中。从大清早到晚上,我们简陋的小桌子前的候诊长龙一眼望不到头,而且,大半是哭得声嘶力竭誓死不从的小朋友。我在兵荒马乱中学会了量耳温、测血压、记录心跳、呼吸和氧饱和度,还在中英文不停切换中使出十八般武艺哄小孩。。。终于,在夜幕降临后处理完全部病患,我爬回宾馆瘫倒在床上,摸着自己保持了十几个小时笑容的僵硬的脸,睡着前脑海中的最后一丝念想是:明天是正式手术了,轮到医生上阵,护士该会轻松点吧。
第二天的现实告诉我这个预期错得有多离谱。
手术从早上9点开始。从手术室神秘大门的后面不断送出做完手术的孩子,推到隔壁复苏室观察生命体征,苏醒后如果没有问题送去病房,有问题的送回手术室抢救。
在复苏室,“带头大哥”麻醉医师勇哥和漂亮的护士美眉对我进行了高强度的岗前培训:重症监护设备、氧气瓶、吸痰器、急救箱、各种麻醉镇痛的针剂-----看得我眼花缭乱。当培训到只在电影里见过的用来做电击的心脏除颤仪的时候,我有点蒙了——难道我们面对的病人还可能出现心跳停止的骇人症状?!
心情尚未从紧张之中平复,第一个孩子已经送来了。护士们一拥而上,从人缝中我看到那一岁多的小小孩脸,满脸满嘴全是血,还有满嘴里缝着的黑黑长长的线,让孩子看起来像是玩偶而非真人,我惊得目瞪口呆头皮发麻。麻醉药效刚过,孩子经历手术之后异常烦躁,拼命哭闹挣扎。护士们有安抚孩子的、有戴氧气面罩的、插各种监测线的、夹指夹的、绑臂带的,在我还茫然失措呆若木鸡时,护士们已经安顿好孩子,开始观察和记录数据。Jean微笑着刚要安慰我一句,第二个孩子又送进来了。护士们立即扑上前去以同样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做完一整套护理措施。
孩子不断被送进来,护士们忙得马不停蹄。我逐渐适应这个节奏,也在翻译之余帮把手,装个氧气罩、挂个输液瓶、给孩子擦拭血迹、换个床单之类的,但心情却一直是心惊胆战状态,不时会看到孩子大口吐血(其实是嘴里的分泌物),或是惊悚地注意到氧饱和度只剩60%,再伴着孩子声嘶力竭的哭声和拼命的挣扎,眼见勇哥举着针管四处救火,我感觉我的心跳和血压都得高居以上!
中午大家瞅空到隔壁迅速解决盒饭,傍晚仍然是轮流盒饭。有时刚吃几口就有病人推出来,护士们扔下盒饭就跑;有时医生做完一台手术出来吃饭时盒饭都已经冰凉;有时我们的病房里也会接待一两个在连续伏案多台手术后脖子和腰实在受不了的医生,在病床上倚五分钟又回去继续战斗。手术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如头天一样,我精疲力竭地爬回宾馆,心里一直在纳闷一件事:当年是谁跟我说审计是最辛苦且高风险的行业的。。。
原以为舍得用掉自己五天
假期做志愿者挺不容易
毕马威除合伙人之外的员工在参加公司的公益活动时是可以用工作时间的,也就是不用占用自己的年假。鉴于我已是老审计员,享受不了这个待遇,于是花啦啦地用掉5天年假做志愿者,自己感觉还挺自豪的。到封开县的第一天晚上与志愿者们互相认识,当我提及用年假来封开时,大家露出了不解的神情,问“难道有人不是用年假吗?”我这才知道绝大部分公司和单位不会给员工用工作时间做公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医生、护士们都是用自己的假期。一个来自中电集团的小姑娘志愿者,全年一共只有5天年假,全部用在这次活动了。从国外来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不仅要用自己的假期,而且有的还自付机票和住宿。我的Jean,来自美国的60岁最美护士,辗转近30个小时来到封开,因为时差晚上只睡着了4个小时,一样和我们从早上6点多坚持到晚上10点。美国的手术医生Ben,已经参加过60多次这样的志愿者活动,去到世界各地为贫困病人手术,在过去的30年从未间断。香港汉基国际学校的几个学生,才16岁,论颜值有颜值,论才华有才华,无论是陪孩子们玩、做翻译,还是各种粗活累活,样样抢着干,中午轮流吃盒饭时“因为不想离开孩子们”他们总是去得很晚,晚上总是医院,让人感觉不到他们自己还是孩子。。。每天和这样的人一起,我感觉自己像上足了发条的马达,大家像一家人,幸福感和满足感爆棚。
活动的第四天恰逢我的生日。忙碌了一天,到晚饭时我跟同样从毕马威来参加活动的John提了一句“今天是我生日”,没想到他笑着说“前天是我的生日”,我刚要对这个巧合表示惊叹,一旁跟我们并肩作战了好几天的美女护士小双接着道“哈,我跟John是同月同日生”。我们不禁相视而笑。我心里想,是谁,为我们做了这样好的安排。
原以为出生时四肢健全
脑子正常是天经地义
这已经是BEAM医疗活动在封开县的第十一次唇腭裂手术了,可是赶来的病人仍然排成长龙。穿着朴素甚至简陋的家长们,怀里抱着、手里牵着各种唇裂腭裂病症的孩子,在队伍里焦急地排队等候,眼睛热切地注视着医生和护士们,也包括我这个穿着医生服的工作人员。我不敢注视他们的双眼,那里面有太多的期盼,孩子的病能不能治好,是不是能赶上这个免费手术的机会,他们急切地想从医务人员的表情上看出些征兆。可我无法不去看孩子们。一些孩子的嘴和鼻子明细畸形,一些孩子从外表上看正常,但一开口却咿咿呜呜说不清话,还有一些孩子伴随有明显的发育迟缓或智力障碍。有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被妈妈抱在怀里,我身边问诊的护士妹妹问孩子有什么疾病,我听到妈妈回答说:唇裂、腭裂、先天性心脏病,还有,两性畸形。我和护士妹妹惊诧地对视,不知该说什么好。而那个身穿旧衣紧紧抱着孩子的瘦瘦小小的妈妈,脸上却不曾显出一丝悲痛,比我们要镇定许多。我心里揣测,也许是在孩子一个又一个疾病被确诊的时候经受的一再打击已经让她习以为常了,也或许是当下她全心全意所关心的只有孩子是否能做手术,已无暇顾及其它。
志愿者们带来了好心人捐赠的玩具,我不停用玩具去安抚受到惊吓的孩子们,但却安抚不了自己的心情。看到因为疾病而显得扭曲的孩子们的脸,看到他们从手术室里出来时哭泣挣扎的样子,看到等待的家长们在听到叫他们孩子名字时焦急奔进病房扑向床头,我意识到,一个人出生时有健全的身体,原来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
医院的楼道里黑乎乎的,两旁堆满了临时加的行军床,厕所里有病人家属在洗衣服,弄得满地是水。我踮着脚尖小心翼翼走在湿漉漉黑灯瞎火的楼道里,突然有几个5、6岁的等待第二天手术小朋友从拐弯处跑出来,高声笑着闹着。听着他们的笑声我突然想到过了明天他们就可能就恢复正常了,相比那些不满足手术条件的孩子、那些不知道有免费手术机会的贫困孩子,其实他们是幸运的那一批。想到这里我浑身轻松起来。再想想我那个自打出生起就精神百倍地天天跟我唱反调,让我头痛不已的健康闺女,我是多么幸运!
原以为“要注意身体”只是
妈妈嘴里老掉牙的叮咛
中间有一天有机会去手术室观摩手术。我雀跃着进去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惨白着一张脸出来,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大半天,魂才回来。不管多么生龙活虎的一个人,不管曾经是好人、坏人、有钱人、穷人,麻醉了,脱光了,躺到冰冷的手术台上,埋在一大堆器械之间,都是一样。我想起了小学时做的青蛙解剖实验。所以,尽我们所能,听妈妈的话,锻炼身体,让自己保持身体和思想的健康,幸福地活着。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