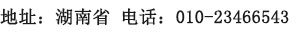一
话说这年的第二场霾,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为什么是第二场?因为下雨前那几天,已经来了第一场。
话说这老天爷,对大西安元年的大西安,也真是恩宠有加,送礼都送两份——七八月的时候,送一份火辣辣的热情,让西安勇夺新四大火炉之首。这才过了三两月,暖气还没咋的供,又送一份浓烈烈的土产,入口即化,直沁肺腑,让每一个大西安人,在腾云驾雾中成了仙,羞了先,然后,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满城尽是蒙面侠的熙熙攘攘中,义正词严地向老天宣战——
终有一天,老夫会练成金刚不坏之身,百毒不侵之躯。
金刚不坏之身,百毒不侵之躯,那不是人,是妖。
没有人能变成妖,也没有人想变成妖。我们既不想变鼻毛比头发还长的妖,也不想成整天腾云驾雾的仙。
我们只想在能看得见南山的蓝天下深呼吸清新的氧气,而不是咔咔着唾出一口口的黑痰还被指二次污染了环境;
我们只想在需要四个轮子奔跑的时候可以自由地奔跑,而不是让我们那屁大排量的车,去背PM2.5或者屁妈的二百五的锅。
可是,对不起,理想很清新,现实很尴尬。
可是,有哪家既贡献了巨额鸡的屁,又贡献了更巨量PM2.5和屁妈二百五的这厂那厂,给我们说声对不起吗?
二
写出以上这些字的时候,我觉得,我又不可避免地犯了抑郁症。
抑郁地都没有心情去笑史。
笑猫啊,起码史人们不用吃灰。
大家不必嘲笑我,也不必同情我,去医院查一下,保不准你们比我更抑郁。
早上一睁开眼,想着车不可驾,不知道该挤哪路公交或地铁才能省时省力,抑郁地便有了赖床的好理由。
好不容易挤进了金枪鱼罐头的车厢,眼瞅着对面零点零一厘米距离的脸面共霾天一色,鼻闻着饱和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韭香与屁味齐飞,抑郁地恨不得飞腿踹车窗。
紧赶慢赶赶到单位,悲催地还是迟到了五分钟,罚款二百块。尼玛一天的工资才几个钱?抑郁地恨不得和老板干架。
累死累活了一天,又反方向重复早上的过程,拖着快散架的身子回到家,迎接你的不是喷香的饭菜,而是老婆或老公哭丧着的脸和孩子的咳嗽声,抑郁地连哭一场的劲都提不起。
医院,面对的又是比庙会还热闹的场面和一个个大孩子小孩子的红脸蛋喘息声,等了几个时辰还未必能见到医生的面,你终于抑郁地一声长叹——
天啊,这所处的,到底是怎样的人间,或者是怎样的非人间。
可惜,这惊天的一问,早被淹没在苍生的嘈杂和污浊的环境,是那么的有气无力。
三
可是,我们依然得抑郁地活着。
在抑郁症之后,又不可避免地犯了尴尬癌。
我们想,如果在秦岭上挖一个大大的风洞,让陕南的清新空气从山那边吹来,雾霾也许能缓解。然鹅,南水可以北调,南氧却没办法北输,这异想天开的想法,和给珠穆朗玛装电梯一样扯。
于是,我们只好一边呼吸着山这边指数爆表的浊气,一边羡慕着山那边的优良,很尴尬。
我们既想享受冬天里的暖气,看见锅炉冒黑烟又忍不住骂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很尴尬。
我们想,政府就知道让屁民们的小排量背锅,为什么就不能关掉哪些贡献巨额污染物的这厂那厂。其实,政府也知道限行既治不了标,更治不了本,他们也卯足了劲去搞什么治污减霾保卫蓝天,但他们更卯足了劲得让鸡的屁像那么一回事,起码得摆出个追赶的面子,构建出超越的里子。
在冬天,包围这里子和面子的,是一个叫雾霾子的大神。可惜,他不是来扶贫问苦送温暖的,他专程来送尴尬。
于是,一切可以刀下见菜的治污减霾办法,没办法行。
于是,现行的限行啊洒水啊遮盖啊向老天用高射炮打尿啊工地停工啊学校停课啊神马的,行了跟没行一样。行了一年又一年,行得雾霾子都忍不住笑了。
在雾霾面前,神马都是浮云。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雾霾已遮天。
于是,我们只能一边骂着老天,一边求着老天——老天啊,您赶紧下一场雪,或者吹一场风,特么地最好来一场风搅雪。
于是,连老天都尴尬地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四
从地理上说,关中还是千百年前的那个关中,西安还是千百年前的那个长安。大地震没有位移它,大战乱也没有抹杀它。
可惜,从环境上说,关中早不是千百年前的那个关中,西安也早不是千百年前的那个长安。
八水依然绕长安,聊胜几股蛤蟆尿。
草堂依然起烟雾,每到冬天更缭绕。
雁塔晨钟依然敲,可惜难见唐僧貌。
骊山晚照依然在,昏昏以为日月倒。
此时此刻,天地间一片苍茫。过去,只有在天将降大雪时,才会是这样的光景。
突然无比向往古人的生活,顺便想起一首和雪有关的诗。
红泥小火炉,
绿蚁新焙酒。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又想起一首歌,送给雾霾中的我,以及你们,我们。
深呼吸
赞赏
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