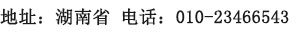一周7天,分钟,急诊科医生孙东辉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年第一周,医院急诊和发热门诊每天涌入多人,是平时的一倍多。医生们相当于不到2分钟就要接诊一个病人。孙东辉耳边除了医疗器械的“嘀嘀”声外,听到最多的就是,“医生,快来。”
文×林樾
编辑×雪梨王
刚给一位老人插上管,孙东辉耳边再次传来急救声。医院医生。
“快!患者高烧、晕厥,呼吸心跳骤停!”同事在一旁大喊。孙东辉冲过去,对患者实施胸外心脏按压。气管插管、使用呼吸球囊,将抢救药物通过静脉注入体内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一气呵成。
几分钟后,患者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孙东辉舒了口气。
这是发生在1月1日晚上8点多的一幕。这些在外人看来惊心动魄的抢救场景,对孙东辉而言早就是家常便饭。这一个多月来,他所在的急诊大厅每天熙熙攘攘,犹如春运。
孙东医院,在华北地区名气颇高,是当医院。疫情政策放开后,医护人员面临的压力更是前所未有。“最近急诊和发热门诊每天都来多人,是平时的一倍多。”孙东辉说,相当于24小时不停歇,不到2分钟就要接诊一个病人。其中近一半患者超过65岁,几乎需要抢救。
正在忙碌的医护人员。摄影:林樾
为了保证这段时间人手充足,医院将多名医护人员“钉”在了急诊和发热门诊上,24小时轮班工作,医院。新的一年开始了,但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改变。
年第一周,仍有数不清的病人从四面八方涌入急诊大厅。
由于没有足够的床位,患者们多会自带折叠床,在急诊大厅找空隙躺下,等待医生问诊。陪同家属一脸茫然地穿梭在密密麻麻的输液架和氧气罐之间。
急诊大厅温度很高。隔着N95和面罩,孙东辉能感受到黏稠的空气吸入鼻腔:“既有病患呼出的气体,也有消毒水和药物的味道,太难受了。”
“医生,快来”快一个月了,孙东辉一直没回家。虽然每天只上8小时小夜班(17点-24点),可他担心将病毒带回家,医院,家里大小事情都顾不上。
这意味着,只要一穿上防护服,就要在8个小时内不吃不喝,也尽量不上厕所。
孙东辉所在的急诊科,是全年、全天不间断接诊的部门。新冠疫情以来,他们既要落实防疫要求,又得保证急诊质量。防控政策放开后,大家本以为能轻松些,可随之而来的是大量阳性患者和有基础病的人。
正式进入急诊大厅前,患者要先在门口预约分诊登记、量体温、测抗原,每一步都有医护人员陪同。这部分工作多由实习生承担。完成这些前置程序后,医生会根据情况,将患者分为5个等级——危急、危重、急症、轻症、非急。前三种病症,救治时间最短不能超过半小时,后两项则至少要等一两个小时,甚至4个小时。
确定等级后,危急病人会被送入单独病房,危重患者则能分到有很多床位的红区病房,急症人员被安置在急诊大厅一侧的黄区病床上,其他人要在大厅里的绿区耐心等待。
也因此,红区、黄区、绿区的医护人员会呈现出两种工作状态——前两个区域一直在插管、上呼吸机、心肺复苏,后者多是查体、抽血、输液。
孙东辉最担心的还是那些危急患者,尤其是感染了奥密克戎的危急患者。
1月2日晚上10点多,救护车送来一位发烧且无法自主呼吸的老人。孙东辉和同事接诊后,马上对其进行紧急气管插管抢救,老人症状稍稍得以缓解。随即,这位老人又检测出新冠阳性,双肺已严重感染。由于该类老人普遍有基础病,抵抗力非常差,会给治疗带来诸多复杂性,孙东辉赶紧联系其他科室进行会诊。
医院的红区病房。摄影:林樾
刚处理完老人的事,急诊又来了一位阳性的主动脉夹层病人。这位60多岁的男性不仅胸部疼痛,血压也急剧下降。并且,他的胸主动脉随时有破裂可能,必须马上手术。于是,孙东辉又赶紧联系相关医生。
处理完这名患者的情况,已经24点了。孙东辉拖着疲惫的身躯和大夜班(24点—早上8点)同事交接,按程序脱掉防护服,给自己全身消毒,开始吃饭、洗漱。
真正入睡是凌晨两点以后了。躺在宿舍的床上,他终于有时间好好看手机——几乎每次下班,他都能收到几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