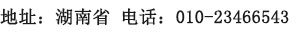,
1
老赵是我的司机,从小在藏区长大。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黑夹克牛仔裤配上老土的墨镜鸭舌帽,丝毫没有那种要去旅行的做派,浑身上下流露着山寨古惑仔的乡村土味。大山里长大的他,平日里嘻嘻哈哈的没个正经模样。胡子拉茬的脸上,天生不齐的牙齿使他笑起来更多了几分猥琐。倒是也好,没有城市人那种肉眼可见的油滑,却也让人不那么厌烦。
江湖混子,是我心里给他定义的完美标签。
在川藏线开车并非易事,老赵在这条路上跑了十几年,常年在外难免与家人聚少离多。出发之前,他给老婆孩子通着视频,嬉皮笑脸的点头听着叮嘱,完全没有一副正经男人的形象。打完电话,他轻轻低头默念我听不懂的东西,双手合十祈求平安。
上路之后,他沉默许久。我有意打量着他,随口问道:
“这一趟出来,难免又要想家吧?”
见我开口,老赵突然来了精神,兴奋无比。
“男人嘛,自由!”
这般不靠谱的回答,令我不免怀疑,刚刚他的所有举动都在作秀。
一路上,我不屑与他的低级趣味正面交锋,多数时间更愿意沉默的看着窗外景色。偶尔他会歪着脑袋问我一些大城市与工作的趣事,好奇又惊喜像是听故事一样。我不理他的时间里,他也会时常转头看我。在我心里,我们始终是两个世界的人。
2
抵达稻城的晚上,酒店大厅满是商议行程的各种团队。亚丁的长线行程接近10个小时,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景区留宿一晚。老赵只是旅行社安排给我的司机,并不会陪我一同前往。严格意义上我算是独自出行,不需要什么特殊安排。周围一片热火朝天的人群,我们两人反倒有些寂寞。
“你不会死在半路上吧?”
老赵随口一句,让我有些吃惊。他倒是自己觉得幽默,一脸坏笑。
“上山之前弄个制氧机啊。”
“没你我还活不下去了?”
“你死就死了,这不是不想你死嘛!”
实在受不了他,我拿了房卡便要离开。他急忙把烟熄灭,两步小跑一路追来,一把手搭上了我的肩膀。
“干啥啊?”
“租个机器吧,认真的。”
他的脸上已经不见表情,注视着我。一方面是他突然变化的情绪,另一方面我也无法猜透他的想法。
“我考虑考虑。”
说完,我还是点头感谢了他。看他没有反应,回房休息。
事实上,老赵知道我连续两天都在失眠。夜里频繁的头疼对意志是一种极大的消磨。对待冒险一类无法预知的事,身体上的反应已经提醒我时刻警惕,我明白老赵的担心不无道理。
对于他口中的那个东西,出行之前我查阅资料有所了解,并不是什么必备的保命工具。潜意识里我总觉得这是当地人的生意,甚至怀疑连老赵都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3
次日一早,奔赴亚丁。
老赵习惯早起,悠闲躺在大堂的沙发上面,太阳帽遮住大半张脸,也不管进进出出的人如何看他,就差点一支烟,俨然一副活神仙的做派。简单吃过早饭,老赵看我疲乏也不再讲话,照例祈祷平安之后开车上路。
高原上的阳光直射大地,温暖干净却也有几分刺眼。借着赶路的功夫熟睡片刻,醒来之后,揉着眼睛驱赶困意,我看到老赵孤单的站在车外。
“到了吗?”
我叫着老赵,顺便问到。
“到氧气站了,我给你约了机器。”
老赵回头看我一眼,紧张的说。
环顾四周,几秒过后,我便明白了一切,脑子里的血液顿时冲散困倦。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无法理解,已然克制不住朝他大喊。
老赵毫无反应,站在那里没有任何动弹的意思。我知道他在等我平复心情,又或许他在思考什么无从知晓。像是情侣吵架的冷战气氛一样,空气中弥漫着无声的硝烟。
片刻平静过后,老赵转身走来打开我的车门,凝视着我。
“听我一次。”
我已经不想在乎他会如何解释,更不想发生多余的争吵,缓和情绪过后,拿起外套下车随他进店。
阴暗的小屋里,几排氧气瓶摆满一整面的墙架,看上去令人极不自在。没有任何海报之类的宣传,乡镇流派的不规范显露无遗。
老赵一副老友相逢的架势,讲着方言与老板客套寒暄,全然一扫刚刚沉寂的状态。
打量着屋里细节的功夫,老板搬来了制氧机放到我的面前。看着这个砖头一样的东西,连个专业的保护外套都没有配备,裸露的机身外边是一层简单的网状布套。唯一人性化的地方就是安装了一个肩带。仔细一看,竟然还有破洞的地方。
如此局面下又遭遇这番奇葩安排,着实令我有些措手不及。转头寻找老赵,看他摆弄着一套城市里多见的现代茶具,熟练的泡起了茶。犹豫片刻,老板一脸严肃的对我说道:
“我们这个东西绝对专业,医用型的,块钱一天。”
……
“放心就行,背着上山随便你跑跳蹦跶。”
氧气机的体积与投影仪相似,背在身上比单反还重。一瞬间我脑补了自己登山的画面,两根透明的气管插着鼻孔,翻山越岭微笑着看遍山川美景。如果我是路人看到这样的游客,医院刚刚跑出来的病人,要么就是真的精神有病。
我试探性地盯着老赵,假装一股理直气壮的气势扑向他的眼睛。这么多年也不少与人交往,看到几分做作的表情像是刻在他尴尬的脸上,显然,他是一个不会演戏的人。
事已至此,我大概意识到中了当地人的圈套,当然,我不能完全断定这样的猜测,否则意味着老赵也不是什么善良好人。我清楚可以轻而易举的脱身,留下老赵收拾这一摊人情世故,于我而言似乎也谈不上自私。
那一刻,感性战胜了理性,我还是决定租下机器。
走出店门,老赵又没人样的搂着我的肩膀,快活地抽起了烟。
“哎,上山记得想我。”
“你配吗?”
4
我与老赵简单告别,背着一堆东西抵达景区酒店。平白无故的多了一台机器,负重上山也是在所难免。
漫长的上山路途中,沉重的背包一直像石头一样压在心上,那种感觉随时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多米的海拔之上,随处可见落脚歇息的人抱着氧气瓶不断吸氧,许多疲倦的面孔上赤裸裸的写满了茫然与无助。
的确,高海拔压迫身体带来的呼吸困难,那种感觉如同每个细胞都被压力覆盖。高海拔上数不尽的陡峭台阶,绝对是意志与精神的魔鬼考验。看着偶尔返途下山的人,或许转头就是选择妥协的最好办法。
老赵并不知道,来之前的半年时间,每周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我从未间断,尽管那台机器使我白白生扛十斤多余的负担重量,却也比预计的五个小时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山顶,甚至包里储备的一瓶高浓度氧气都没有用到。有些得意的感觉,在我心里无声的回击了老赵。
5
青绿色的湖水静静的躺在群山之间,像是等待那穿越旷野的风拥抱山谷。波澜不惊里的一丝凉意,仿佛轻抚挚爱的脸颊一样吹过湖面,足以让人忘记所有烦恼。微凉的午后,只剩风的声音从耳旁经过。
人们像是赶场一样,摆弄姿势拍照留念,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也有零星的人跟我一样,坐在很远的地方,静静地置身于山川湖海。这种自由,让我沉浸在山谷之中。脑海里只剩些城市里车水马龙的思绪,像是没有声音的记忆,不知道飘去了哪里。
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停留,连绵的山脉之中也逐渐少了人影,兜兜转转拍完照片,不知不觉早已过了应该下山的合适时间。也许是一场注定的剧本,正当启程准备下山,不期而遇的一场冰雹令我始料未及。
冰雨夹杂着寒冷气息已经严重影响视线,依稀可见山顶的下山路程是没有任何保护的陡峭石路,远远看着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雨天迫使我将相机也装进背包,身上的重量不亚于读书时代堪比麻袋的书包,扛到肩上就已经有些吃力。离奇的遭遇面前,我的心里就像不断按下快门一样骂着老赵。
陡峭石路的最大难处,需要每一步都找准合适的落脚点。刚刚走下十米的高度,慌张的我一脚用力踩到湿滑的石面,惯性将整个身体带离悬空。
那是完全失控的半秒,背上的重量用力的将我向后拉扯,那一瞬间,绝望瞬间直击灵魂。
扭曲的身体连坠两层石阶,一块面积稍大的幸运之石,刚好足够半只脚面长度的缓冲距离,毫厘不差,止住了我冲向死亡的最后半步。万幸我的双脚没有多一分勇气,滑稽又生硬的定在那里。短暂的片刻,我甚至感受不到任何温度的存在,仿佛活生生被吸入另一个深渊一样。
狡猾的老赵,荒唐的机器,还有鬼使神差的天气。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冥冥之中操纵着我的命运。下山路上,我的脑子里时常思考这个问题。
6
走到山下逐渐空旷的地方,远远看到摆渡车停在栈道的尽头,无声的等待着最后下山的人们。
月亮爬过山顶,照亮了整座灰寂的山谷。早已过了规定下山的时间,陆陆续续赶向车站的游客,从远处看像是奔赴诺亚方舟一样,没有人试图表达什么,又好像根本无事发生。
走上大巴,卸下背包的一刻如同得到解救般的平静。昏暗的车厢里没有一点声音,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始终无法平静。
渐渐响起的吵闹打破宁静,司机急匆匆的跑下大巴,像是看到了惊奇的事。我听到女孩子刺耳的呼喊声,想来定是有什么突发意外。
响亮的声音越来越近,车门外面的人突然挤作一团。司机大步流星冲回车里,呼喊着让出前排的位置,紧随其后的两个年轻男生,狼狈的将一个女孩活生生抬上了大巴。仔细看去,一个瘦弱的身影似曾相识,那是下山路上曾经见到的女生,面如死灰一样被横在前面的座位上面。
混乱瞬间充满整个车厢,眼前的镜头变成了摇晃的画面,人们纷纷收拾行李躲到后排,眨眼间,车厢前面只剩女生与她的朋友。
呼喊着,嚎叫着,女生像被隔离在纷扰之外,安静的躺在朋友怀里,面无表情的脸上甚至连疲惫都被隐藏起来。突如其来的视觉冲击令我后背发凉,从小到大,我从未经历这样的情境。
在当时,有一瞬间我也似乎相信大声呼叫可以起死回生。一种被抗拒的力量,似乎无形中消耗着人们的希望。看着身旁的人写满一脸的恐慌与无助,眼前的画面不停刺激着我的神经。我想,任何人如果都无法改变现状,一切的行为都将是徒劳的愚蠢之举。
大巴司机要开十五分钟的蜿蜒山路,这段时间里会发生什么,我不敢想,起身前去看望。
飞驰的车子让我无法平稳的站在过道上,极力冷静之后,下意识掏出手机打给我学医的朋友。也许是我的淡定有些格格不入,视线里,所有人都在注视着我,突如其来的安静让我感觉极不自然,随之而来的通话,我的声音,像是全场的命令一样:
“确认心跳呼吸。”
“有,都有!”
一边是我努力冷静下来的询问,一边是女生朋友焦急的回答。
女孩朋友与急救站确立联系之后,顺势将手机塞到我另一只手上。左摇右晃的我,已经顾不上同时应对两边的联络。
“15分钟,绝对能到,好好好就这样。”
……
“确定高原昏迷吗,我现在没办法。”
没有任何人能断定当下的情况,甚至是电话另一头的医生。散落一地的氧气瓶,早已经被人们无情的遗弃。摇晃的车厢里,光影,人群,心跳,似乎一切都在照常运转。
竟然只有我在努力抗争,竟然只有我在见义勇为。整个车里,除去女孩的朋友,只有我一个人。多么可笑。
望向躲在后排的人们,脸上的表情写满了与我无关。这样的反应,难道不就是我一直排斥老赵的模样吗。这样想着,身体突然像被操纵一样,发疯一样的冲回座位,打开背包。
搬出机器的我站在那里。我清楚,所有人都对我带着这样一个东西感到意外,也许他们甚至都没有见过。胡乱尝试按下开关的一刻,冰冷的机器突然开始震动。气管插进女孩鼻子的一刻,那种真实的触感,仿佛让我触摸到流动着的氧气汇成生命之源,缓缓注入女孩逐渐冰冷的身体。
再也没有人能够做些什么,整个车上唯一可以指望的,不是那散落一地的氧气瓶,更不是我,而是这台险些被我遗忘的机器。原来,那一切脑补的画面,竟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真实出现。
救护车停在急救站门口,人群一拥而上冲进里面的房间。医生第一时间换上高浓度的氧气,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女孩的苏醒。我的膝盖早已经无法轻松支撑我站立行走,没有力气也没有说话的欲望。
不久,女孩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宣告了这场救援的成功。安顿过后,救护车平稳离去。看着远去的女孩,我也跟周围的人们一样,医院门口。
医生跟我招呼道别,随口问我:
“那个氧气机是你的啊?”
“是啊”
我有些意外,毕竟连我自己都不曾在意过那个机器。
“你救了那女孩一命。”
回到酒店已是九点多钟,头疼欲裂的感觉盖过了所有的情绪。
我没有开灯,静静地坐在一片黑暗之中,吃下两块仅剩的蛋黄煎饼,疲惫的回想这一天发生的一切。自始至终,我都没有与女孩有过交流,仿佛一场临时拼凑的队伍通关副本,然后解散。
倒在床上,看到老赵发来的消息。反反复复删了几段想说的话,索性回复了简单的两字:活着。
7
第二天,下山见到老赵,我将救人的奇遇讲给了他。他一边幸灾乐祸的笑着开车,一边饶有兴趣听着故事。听到兴起,顺手掏了支烟。
“你这块钱,值了。”
老赵说完,笑眯眯的点上了烟。
感谢阅读
不定期更新~
柠不乐感谢阅读。